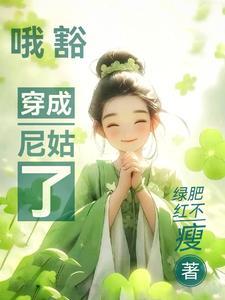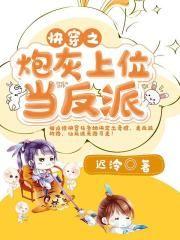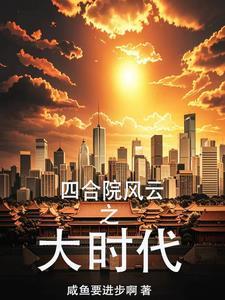魔爪阅读>明末:我的金手指是现代大国 > 第205章 入京前的硝烟(第1页)
第205章 入京前的硝烟(第1页)
崇祯六年,大明未显败亡之象,但流寇鞑子,天灾频频,亦让大明疲于奔命。
南直隶一座小县城之变,带来的是朝廷开始巨变。
小院内。
官元震等汇聚。
“柳家被灭族,魏昶君此人手段不凡。”
“不错,柳安陆前脚商议联合宣党对魏昶君下手,后脚便遭族灭,此人不光手段狠辣,耳目更是灵通。”
“与先前一般,无论是假借流贼还是山匪,此人始终在幕后行事,拿不住此人把柄。”
一众浙党官吏神色凝重,思考如何对付。
“既然魏昶君为安化之乱冠名山匪,那发兵剿灭山匪,压制暴民,也在情理之中。”
“山东齐党素依附吾等,如今冒出个刺头,是该好好管教管教。”
“也让天下人看看,似魏昶君这般人,下场如何!”
话音落下,一时间,众人神色狠辣,大笑点头。
柳家背后为浙党。
党争是明末历史中不可忽视的部分。
浙党最初和东林党均为南直隶势力,这是朱棣昔日迁都遗留,加之洪武年南北榜之争,最初双方都以维护南方士子,针对北方取仕为核心,换言之浙党本和东林党拥有相同利益。
初始浙党不参与党争,但因东林党顾宪成纠集官吏,针对浙党首辅赵志皋对小岛贼寇议和,更屡次排挤政见不同官吏,在沈一贯登上首辅位后,开始抱团亲近权贵,与东林党分道扬镳。
此次东林党对魏昶君于山东三府之地实行一条鞭法熟视无睹,浙党更是坐不住。
昔日万历二十四年拒绝矿税,竟公开对抗皇帝,足见浙党对利益重视。
如今柳安陆为浙党中坚,竟遭族灭,无论是为自身利益,为稳定浙党人心,还是为针对东林党,对付魏昶君都势在必行。
更何况,若山东齐党各官吏不再依靠浙党,只怕对抗东林,又少了几分胜算。
朝堂上,奏疏频频。
鞑子欲吞并蒙古诸部,国力再增。
大同府流民疫症遍传,请求赈灾。
云南土司频频挑衅官府。。。。。。崇祯神态疲惫,愈发察觉时局维艰,颓势渐显。
王承恩见状,询问还有何事上奏。
“臣有事奏!”
“日前南直隶传驿,安化县暴民裹挟山匪作乱,袭杀城中贤良世家,致柳氏满门几族灭,其后山匪暴民盘踞此城,实与流贼无异。”
“臣请朝廷发兵入城,将此暴民贼寇尽数诛杀,斩首示众,以正王法,以儆效尤!”
“臣附议!”
“为社稷安危,当防微杜渐,以防流贼之乱重蹈覆辙!”
在官元震示意下,几名浙党官吏纷纷上奏,义愤填膺。
浙党很聪明,谁也没提魏昶君。
毕竟有些手段在暗地里玩可以,但不能拿到台面上。
朝堂似乎有一面倒之趋势,崇祯皱眉,神色冰冷。
鞑子流寇不足为惧,但朝堂之上结党营私,昔日阉党已除,如今东林,浙党两党如日中天,他愈发不悦。
区区一县之地,他并不在意,相比之下,他倒是更讨厌朝中官吏动辄呼风唤雨,以势压人。
尤其是这些南直隶官吏,仗着朝廷两都,在南直隶根深蒂固,权势愈大。
只是此刻崇祯放眼朝堂,唯一能与之抗衡的东林党眼观鼻,鼻观心,老神在在,低头不语。
让他眼底阴戾夹杂几分怒意。
东林党不出手,皇权亲自下场,更为被动。
“臣有事奏!”
“安化之变未有夺城,臣来时差人打探,乃柳家欺压佃户,刻薄下人之乱,何况一众奴仆取走奴契后,再未生乱,回家种地去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