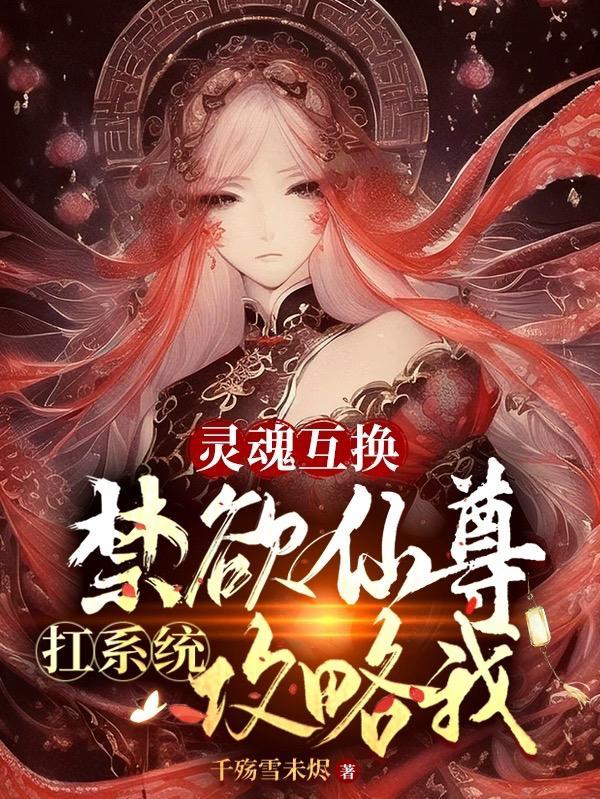魔爪阅读>柯学的格瓦斯在线阅读笔趣阁 > 第575章(第1页)
第575章(第1页)
“青峰,上一场比赛很精彩。”
“!!黑子?!你什么时候来的!”
“我一直都在。”
“志保,我之前提的那件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?”
“我不去美国。”
活着的人们,各自奔向自己的未来。
……
黑暗中,一个人潜入深眠治疗室,悄悄将手伸向——
“嗷!”春教授触电般地收回了手。
灯亮起,面如寒霜的宫野教授手持长尺站在操作台旁:“你是急不可耐要去踩缝纫机了。”
“理论上她该醒了,却没醒,我关心一下治疗参数有没有搞错,不是应该的吗?”春教授理直气壮。
宫野教授正要让她滚蛋,却见她一脸不可思议地伸手向自己身后,“少来这套,今天——”
“0号哨兵意识体修复完成。”ai缺乏感情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
归处与重逢
从葬礼回来的当晚,萩原研二就病了。
要不是他现在跟幼驯染一起合租了一套公寓,没有继续住警视厅单身宿舍,恐怕得被急救车拉走。
萩原千速匆匆赶到医院:“怎么回事?”
“早上不起床,发现他发烧了,摸额头感觉温度不算很高,但怎么都叫不醒,”松田阵平皱眉道,“送来医院,体温降下来了,又梦魇呓语……医生说这像是儿童受惊或者长期心理压抑情况下才会出现的症状,我问了过去的同事,这段时间明明好好的。”
拆弹警察是高危职业,萩原研二就是在毕业后不久的一次拆弹中重伤躺平7年,但这样的高危情况又不是每一天都会发生,算上今天他才返岗满1年,上级也没有丧心病狂到让他立刻重返拆弹一线,除了抓捕黑市商人,做的最多的就是培训新警员、向民众宣传防爆、检查易制爆化学品生产销售等等,都是些后方工作,最近一段时间东京市内也没发生任何造成人员伤亡的爆炸,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分析,都找不出他受惊、心理压抑的原因。
但躺在病床上的萩原研二紧锁的眉头,模糊的呓语,时不时渗出的虚汗,都在表明他此刻正在备受折磨。
搜查一课太忙,萩原千速让松田阵平回去,自己一个人照顾弟弟。
去食堂解决午饭时,遇到了上司横沟重悟的孪生哥哥参悟,他也是来医院照料家中长辈,两人聊了会儿,自然也聊到了萩原研二奇怪的病。
横沟参悟摸着下巴:“萩原小姐的弟弟昨天有没有去过什么阴森的地方呢?比如废屋、墓地什么的。”
萩原千速愣了愣:“他陪我去参加了朋友的葬礼……”
“这就对了!”横沟参悟左手握拳砸在右手掌心,“他一定是被葬礼吓着了!我参加曾祖父葬礼第二天也病倒了,症状跟他差不多!”
萩原千速嘴角抽了抽:“横沟警官那时多大年纪?”
“三岁。”
“我弟弟三十岁了。”萩原千速叹气。
“啊这……”
虽然觉得横沟警官的“葬礼惊吓论”很扯淡,但回到病房,萩原千速还是忧愁起来,她伸手轻抚弟弟皱紧眉头:“研二,究竟在难过些什么呢?”
没有人知道。
所幸萩原研二没有昏睡太久,早上退了烧,下午就醒了。
“估计是着凉了,”刚苏醒的萩原研二故作轻松地安慰姐姐,“我没什么事,回家吧。”
萩原千速不信,但医院检查结果显示的确如此。
萩原研二顺利出院。
爆炸物处理科的女警们是最早一批发现问题的人。
活泼俏皮,幽默风趣,风流多情但绝不会冒犯到女性的萩原警官,似乎陷入了难解的忧愁中。他不再每天元气满满地跟每一个人打招呼,不再时时挂着让人见之欣喜的感染力十足的笑容,不再体贴地关照每一个身边的女性。
第二个发现的自然是松田阵平。
“啊!”萩原研二一声痛呼捂住脑门,惊讶地看着握着一次性筷子面色不善的幼驯染,“小阵平,你干什么?”
萩原研二可怜兮兮地控诉幼驯染的暴力行径。
“是我该问你干什么。”松田阵平板着脸摘下墨镜瞪他,“这是你今天第几次走神了?你拆弹的时候也这样?”
“当然没有,hagi是个合格的拆弹警察,”原则问题萩原研二当然不能认,“跟小阵平在一起不用这么紧绷着嘛。”
前半句倒是真的,松田阵平也找小林警部打听过,萩原研二的工作的确依然完成得很好,没有受他奇怪的精神状态的影响。
“所以你到底怎么了?”松田阵平质问,“莫名其妙病了一场之后,你就跟换了个人似的,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,每天都能叹一百回气,车展、联谊、桌球,以前什么活动都少不了你,现在都不去了,不是把自己关在屋里发呆,就是一个人跑去没人的地方瞎逛——你到底有什么发愁的事,说出来不行吗!”
松田阵平声调越来越高,他一拍桌子:“就算我解决不了,还有千速、班长、降谷他们,难道大家都不值得你信赖吗?!”
“小阵平,我……”萩原研二语塞,他叹了今天第一百零一次气,“我不知道。”
萩原研二知道自己的异常,也知道身边亲友们都在担心他,但就他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是哪出了问题,又如何求助、解决呢。
他像个不知道哪里漏了的气球,元气和好心情每时每刻都在从缺口逸散,让他像一个半瘪的多啦a梦气球一样永远耷拉着脑袋。
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,”萩原研二垂下了眼,“我就是……不快乐。”